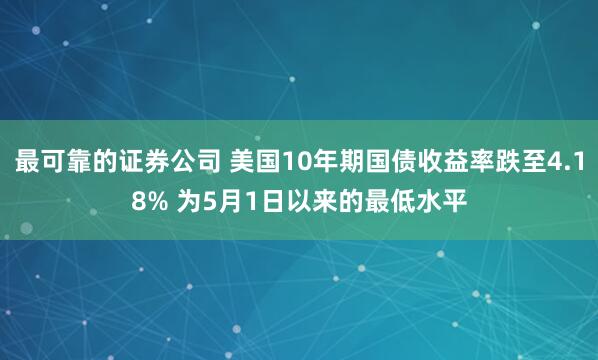伊朗作为古代文明的起源地之一,连接了西方的地中海、东方的中国、北方的欧亚草原和南方的印度河流域,在古丝绸之路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中国考古大讲堂》第四季“中外联合考古”系列讲座中,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伊联合考古队中方领队张良仁讲述了中国考古队首次进入伊朗高原进行考古发掘的故事,揭示了古代中国陶瓷向西亚传播的历史细节。以下是讲座主要内容。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伊联合考古队中方领队张良仁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伊联合考古队中方领队张良仁
『为什么要去海外考古』
2016年3月,南京大学与伊朗文化遗产和旅游研究所签订了为期5年的合作协议。同年11月,中伊联合考古队开始发掘位于伊朗北呼罗珊省地区的纳德利土丘。这是中国考古队首次进入伊朗高原,与伊朗同行携手合作进行考古发掘。
经常有人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有那么多考古工作要做,你们为什么要去伊朗帮助外国人进行考古发掘?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研究中国考古需要借鉴外国考古。中国并非封闭的区域,而是自古以来与外部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北面与欧亚草原、俄罗斯,西面与中亚、西亚,南面与东南亚、印度,东面与朝鲜半岛、日本等都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我们在考古发掘中经常会发现罗马的货币、波斯的银币、印度的佛像等,要理解、研究这些历史文物,就需要了解外国的考古资源和资料。同时,通过海外考古,了解中国周边区域的考古情况,可以使我们重新认识自身的历史。比如,我今天讲的中国古代陶瓷如何走向西亚这个问题,就是通过研究从伊朗发掘的陶器,反过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陶瓷的发展脉络以及中国陶瓷对世界作出的贡献。
第二,赴海外考古是学术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政治、经济交往外,学术界也要走出去,到世界各国去。通过与外国政府部门、高校师生以及普通民众的广泛沟通,能够增进彼此的了解,开展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
第三,提升中国考古的国际化能力。当下,在亚非拉地区,很多国家的考古发掘能力较弱,缺乏经费和研究人员,如果没有外来的支持,几乎无法开展考古工作。而中国考古历经百年的发展,尤其是近几十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考古事业、考古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使得我们的研究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目前我国在考古技术、设备等方面与西方国家水平接近,具备了走出国门开展考古工作的条件,可以为全球考古贡献中国力量。
『丝绸之路的“发动机”』
伊朗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史称波斯。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独特,其东边隔着阿富汗与中华文明相望,西边为地中海世界,有希腊文明、罗马文明以及埃及文明等,北边是欧亚草原的游牧文明,南边是南亚的印度河文明。伊朗恰好位于这四个板块的交会之处。
中国与地中海分别位于丝绸之路的两端,南亚、欧亚草原、伊朗则处于丝绸之路的中段。在历史上,中国人、欧洲人通常是不跨越丝绸之路的,而在这条路上行走的主要是伊朗地区的人。所以,我把伊朗称为丝绸之路的“发动机”,正是这些伊朗地区的人在四大板块之间穿梭往来,传播各种器物、食品、科技、艺术以及宗教等,为丝绸之路的繁荣注入了澎湃而持续的动力。
伊朗与中国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颇为久远。较早关注古代中国和伊朗之间文化交流的学者是一位叫作贝特霍尔德·劳费尔(1874年—1934年)的美国东方学家。他出生于德国,懂汉语、波斯语、梵语、马来语和蒙古语等多种语言。他曾赴中国考察,还写了一本书叫作《中国伊朗编》。在该书中,他利用文献材料来研究汉代以后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各种植物,论证了苜蓿、葡萄、开心果、石榴、芝麻、亚麻、黄瓜都来自伊朗。他夸赞中国人有非常开放的心态,能够吸收外来的一切美好的东西。
在中国也发现了有关古代中国和伊朗交往的实物证据,我举两个例子。
一件是1955年发现于西安市西郊土门村的一块唐代墓志,这块墓志采用汉语和伊朗中古时期的巴列维文两种文字书写。墓志的主人是苏谅的妻子马氏,马氏和她的丈夫苏谅都是波斯人的后裔。他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呢?唐初,波斯萨珊王朝遭受阿拉伯人攻击,萨珊王朝的王子率领使团来到唐朝,请求唐朝派援军拯救萨珊王朝。之后,王子及其使团成员便留居长安生活。他们信仰拜火教,还在长安修了一座拜火庙。苏谅和他的妻子正是使团成员的后裔,这方墓志见证了波斯人在长安长期居住生活的历史。
另一件文物是“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此碑于唐建中二年(781 年)由波斯传教士伊斯出资在长安大秦寺建成,碑文描述了景教传入唐朝并在唐朝流行开来的历程。中国古称东罗马帝国为“大秦”,称最初传入中国的基督教为“景教”。唐贞观九年(635年),来自波斯的景教传教士阿罗本抵达长安,获唐太宗接见,并获许在长安建立景教寺院,准其传教。至“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竖立之时,景教已在中国活动了近150年,开枝散叶,持续繁荣。该碑于17世纪被重新发现,它是中西文化交流及早期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见证物。
 伊朗纳德利土丘全景。 图片来源:公众号“西北大学伊朗研究”
伊朗纳德利土丘全景。 图片来源:公众号“西北大学伊朗研究”
『发现仿烧的伊朗青花陶』
中伊联合考古队挖掘的是一座名为纳德利的土丘遗址。土丘在中亚、西亚、南亚和欧洲都非常普遍,它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由一层一层的建筑废墟堆起来的。纳德利土丘大致呈圆形,位于伊朗阿特拉克河的上游河谷,规模巨大,最大直径达185米。它在地面上的高度是20米,地面下的深度有8米。
古代的丝绸之路是一个道路网络,其中有干线也有支线,纳德利土丘遗址就位于干线上。这条干线是从土库曼斯坦、阿富汗一路延伸过来的。纳德利在波斯语中的意思是国王的或是与国王有关的,可惜纳德利土丘在伊朗的历史文献中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我们只知道,在19世纪伊朗有个王朝叫恺伽王朝,恺伽王朝有一个纳赛尔丁国王,他曾经率领一支访问团来过这个遗址,随行的有摄影师和文书,摄影师拍了一些照片,文书描述了这个遗址的情况。按照描述,这个土丘的上方曾经有一座城堡,周围有一圈城墙。而现在,城堡已经杳无踪迹,只留下一小部分城墙。
我们于2016年和2018年分别进行了两次考古挖掘,挖了一条很长的探沟,总长为44米。依据前期的发掘成果,这座土丘的使用年代从铜石并用时代一直延续到伊斯兰时期,前后近5000年。
纳德利土丘下面的沉积物厚度达8米,我们在沉积物表层发现了一个灰坑,深度为2.5米,底部直径超过3米,其形状像一个袋子,我们称之为袋形坑。从这个袋形坑内,我们发掘出若干器物,一部分是青花,一部分是孔雀绿釉陶。
这些青花的纹样和颜色乍看之下与中国青花瓷极为相似,其器型也是中国传统的盘和碗。但是若仔细端详,会发现它并不是中国青花瓷。中国青花瓷是用瓷石和高岭土烧制的,所以中国青花瓷的胎是白色的。但这些伊朗出土的青花,观其胎,发现其中有黄色、白色、蓝色的物质。因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伊朗仿烧中国青花瓷的本地产品,我们将其命名为伊朗青花陶,因为它并非真正的瓷器。
通过对这些青花陶和孔雀绿釉陶的碎片进行热释光分析,并对一同出土的兽骨进行碳14测年,确定其年代为1721年至1818年。虽然其年代离今天只有200多年,但是它们对研究西亚仿烧中国陶瓷的历史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我们把这些青花陶的样品送到了故宫博物院,分析其胎和釉的组成成分。经检测,它的釉、着色剂、胎都和我们中国的瓷器不一样。其胎里的黄色物质为黏土,白色物质为石英,蓝色物质为玻璃,也就是说,这些青花是用一种由沙子、黏土与玻璃组成的合成材料进行烧制的。这种材料在1301年的伊朗文献中曾经有过记载。一个名叫阿布卡西姆的人写了一本书描述当时伊朗一个叫作卡尚的制陶中心,在书中,他提到了一种制陶的合成材料——10份沙子、1份黏土加1份玻璃。这次发现的胎和这种配方非常接近。我们的分析结果是,伊朗青花陶的胎体主要由棱角分明的大石英颗粒构成,石英间隙中填充着黏土和玻璃,这种胎应是伊朗本地的熔块胎。它的釉也是伊朗本地的高碱熔块釉,即经过研磨的石英与碳酸钠熔融在一起的混合物,并在其中加了一些碱。
此外,其中的着色剂成分分析表明,这些青花陶含有铬、铁、钴和锰,而中国青花瓷含铁、钴和锰,不含铬。这种铬也是伊朗本地的一种颜料,伊朗有专门的铬矿。
『伊朗窑工的创新之举』
那么,中国青花瓷是什么时候开始外销到伊朗的?西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仿烧中国青花瓷的?他们又有什么样的技术创新呢?
中国自唐朝已出现青花瓷。1975年,扬州考古首次发现唐青花瓷器碎片。经检测分析,其中含有钴、锰、铁等成分,与唐三彩的成分较接近,其年代为唐中晚期。2003年,河南巩义黄冶窑址出土了唐代青花瓷片及蓝彩白瓷,经成分检测与扬州出土标本一致,确认该窑为青花瓷产地。
 唐“黑石号”沉船出水的青花盘。(蒋迪雯摄)
唐“黑石号”沉船出水的青花盘。(蒋迪雯摄)
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现的唐代沉船“黑石号”上,出水瓷器总计达6万多件,其中有3件完好无损的唐青花瓷盘,但是其颜料、纹样皆与中国传统瓷器有所差异,显然是受到了西亚文化的影响。这艘沉船的一件瓷器上附有“宝历二年”的铭文,“宝历二年”即公元826年。此船应是在826年之后起航,出发地可能是广州或扬州,前往西亚波斯湾的一处港口,可惜中途在印度尼西亚葬身大海。这意味着,唐代晚期青花瓷已经出口外销。这些唐青花瓷盘以白地蓝花为特征,装饰有阿拉伯式花草纹,其独特的造型和装饰风格表明,它们可能是专门针对西亚市场定制的商品。
中国的瓷器为什么在西亚、欧洲乃至全世界广受欢迎?主要有两个原因:一、好看,美观;二、表面光滑,易于清洁。中国陶瓷业之所以发达,得益于中国拥有极为丰富的瓷石与高岭土资源。然而,类似的原材料在伊朗及西亚颇为匮乏。伊朗虽然有高岭土,但它的开发利用较晚,瓷石更是完全没有。伊朗以及西亚较为常见的原材料就是黏土、沙子以及玻璃。于是,当地窑工为了仿烧中国青花瓷而实施了一系列技术创新。这也是让我们为之着迷的研究课题。
他们要仿烧中国的青花瓷,首先需要在瓷器上施一层白釉。怎么获得白釉呢?公元9世纪以前,西亚地区流行的陶器多为孔雀绿釉或蓝釉陶器,其胎料为黄色黏土,釉料为铅釉,且在釉中添加了绿松石或孔雀石。为了仿烧中国青花瓷,他们发明了一种名为锡釉的釉料,即在釉中加入少量锡。如此一来,釉色便呈现出白色。它的胎还是黄色的,胎体的原料还是当地的黄色黏土,但是它的釉是白色的锡釉。随后,他们又在白釉之上运用钴、铁、铬等原料绘制纹样,进而形成了青花陶。
这其实是一项技术创新,旨在获取与中国陶瓷相类似的美观效果。
 故宫“璀璨波斯——伊朗文物精品展”展出的阿拉伯花纹青花抱月瓶。 (视觉中国供图)
故宫“璀璨波斯——伊朗文物精品展”展出的阿拉伯花纹青花抱月瓶。 (视觉中国供图)
『破解中国瓷器的“奥秘”』
中国的唐青花瓷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一度中断,一直到元代才重新开始烧制。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复烧时间是在14世纪初。目前考古学家在景德镇发现了几处元代青花瓷的窑址,比如湖田窑、珠山御窑厂。在出土的青花瓷中,有的纹样是中国传统样式,有的则受到西亚文化的影响。
在元代创烧以后,青花瓷很快又出口到了西亚。目前元代瓷器在国内留存数量稀少,但是在西亚,有两处地方留存了一定数量的元代瓷器。
一处是伊朗的阿达比尔陵寺,这是一座清真寺和王陵合二为一的建筑。它建于公元16世纪的萨法维王朝,这是国王阿拔斯一世为祖先修建的王陵。陵寺中有一处建筑,其译名是瓷器宫或中国宫,墙上有一个个壁龛专门用于收藏中国瓷器。在阿达比尔陵寺所收藏的1100多件来自中国的瓷器中,有37件为元代瓷器,其余大部分为明代和清代瓷器。另一处是土耳其的托普卡帕宫,收藏了40件元代青花瓷以及明代、清代的青花瓷。
除青花瓷外,西亚窑工还仿烧中国的白瓷以及龙泉瓷。他们想达到又薄又坚硬的效果,但由于他们没有瓷石,便研发出一种新材料,我们将其译为熔块胎或砂胎、砂玻胎。这种胎最早是在伊拉克发明的,发明的年代是在公元9世纪。然后,到了11世纪,在埃及得到完善,又传回到伊拉克并推广开来。这种胎后来成了西亚烧制高档陶器的原料,能够达到又薄又硬的效果。
无论是在伊朗、伊拉克还是在土耳其,西亚窑工早年仿烧中国陶瓷时,试图复制中国陶瓷的器型、颜色和纹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再满足于单纯模仿,而是着手研发符合自身需求、本地人喜欢的器物。明清交替之际,中国的陶瓷出口大为减少,由于伊朗仿烧的陶器质量上乘,足以与中国瓷器相媲美,他们甚至冒充中国瓷器出口至西亚其他国家以及欧洲地区。
在西亚之后,欧洲人也开始仿烧中国陶瓷,起初他们借鉴了西亚的制陶技术,如锡釉和熔块胎来仿烧中国陶瓷。至18世纪初,德国人成功破解了中国瓷器的烧制奥秘。起初,他们也是仿照中国外销至欧洲的瓷器进行烧制,后来逐渐开始研发符合本国民众喜好的器物,例如人物塑像、茶杯、咖啡杯等。德国之所以能够破解中国瓷器烧制的奥秘,得益于他们召集了众多科学家,涵盖化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等,对中国瓷器进行全方位的分析。自那时起,陶瓷科学应运而生。至18、19世纪,受工业革命影响,欧洲的陶瓷生产逐步走向工业化。至20世纪初,随着欧洲的陶瓷工业生产设备传入中国,反过来又带动了中国陶瓷的发展。
陶瓷的世界很精彩最可靠的证券公司,也很复杂。陶瓷串联起了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明,呈现出中国和西亚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展现出不同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的华章。中国陶瓷走向西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未来我们还会继续研究,因为其中还有很多的谜团等待着我们去破解。
利鸿网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